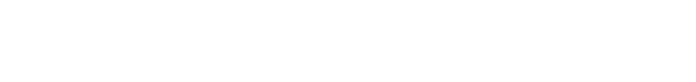张长国
年味是一种味道,那么,年味的颜色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季节的原因,腊月的颜色是银色的,一声声脆响的鞭炮声送来的年味却是红色的,在满地红的碎屑中,年,正如一个归家的游子,带着火红的热情、丰厚的节礼,还有那久别重逢的喜悦,急匆匆来到了家的门口。与之相随而来的,还有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情、思归的乡愁,以及那红彤彤的年味。
春节前的集市上、超市里、家庭里……红彤彤的中国结、红彤彤的春联,连人们脸庞上的喜气也是红彤彤的。买几斤年肉、挂几幅年画、请来的财神和灶君,上面都少不了红彤彤的颜色。红色,是中国的吉祥色,连大人和孩子买的新衣服,也是以红色为主呢!就连腰带,有的人也是用红色的,红彤彤的喜气就这样束在了腰上。
红彤彤的年味,是那些高挂在杆头的满地红鞭炮。听,“噼啪!噼啪!”“嗵,啪!”随手丢、二踢脚,犹如阵阵有节奏的叩门声,几下就敲开了腊月的大门。年味,就是这鞭炮清新的硝烟,将年味熏了个透。在鲁西南的乡村里,孩子们最爱燃放的是一种每盘一百个的“火鞭”,每个大约有豆秸粗细,两寸来长,大红的包装。胆小的孩子把它夹在墙缝里、放在土路上、人家的窗台上燃放;胆大一点的孩子,把鞭炮放在北风吹得爽净的大路旁,上面压上一只马口铁盒子,炮捻子露出盒子,点燃了,远远地跑开,回头看那盒子时,只是一声“嗵”的闷响,马口铁盒子就被爆炸的气流抛上高空,地上,留下了一地红色的纸屑。年味,就这样裹挟着鞭炮声、孩子的笑闹声而愈发浓厚起来。
“民以食为天”。年味里,怎么能少了红彤彤的吃的呢?“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枣花糕是鲁西南特有的面食。前一天的晚上,家里的主妇们就把那些中秋节时打下的干枣儿收拾出来了。晾了几个月的木铃、翠铃和布袋枣儿不软不硬,都已经是半干的时候,红彤彤的枣儿在温水里泡上半宿,喝足了水儿,个个浑圆饱满,恢复了神气。发酵了的新麦面团微微渗透着些微黄,散发出阵阵麦香气。面团被拿上那块白崭崭柳木的面板,被一双双细嫩的巧手碾来滚去,变成一根根重重叠叠的厚条儿,一扭一捏,枣儿就包在了面条里,好似一个婴儿睡熟在了新棉花做的襁褓里。襁褓不断变多,最后都被安置到了一块大而圆的新大陆上,等待火的温度和热情把它们唤醒。出锅了,枣子的香气、新麦面的麦香,夹杂着农家土灶燃烧的麦草味儿,一道儿冲进人们的口鼻,又散发到干爽的农家小院中。随着一声“枣花糕起锅了!”的喊声,一百零八个枣子的枣花糕映射出一片红彤彤而又祥和的年味。年味,就藏在这舌尖上的美味中。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大年三十,吃过午饭,正是贴春联的时候,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像赶趟儿似的出来了,老年人端着面粉打的糨子,小孩子搬板凳,揭下发白变色的旧春联,用高粱秸炊帚蘸着糨子刷上木制的门框,趁着热乎,把春联一展一捋,平平展展就贴上了。大红的灯笼一边一个也挂起来了,在人家门楼檐角下摇摇摆摆,似乎是灯笼摇动带来了些微的寒风,风里又带来些煎炒烹炸的美食气味,从一处处农家小院里飘进飘出,一时间,整个村庄都被这祥和的味道所围绕。这时候,最高兴的要数每家的孩子,玩累了,疯够了,回家拿起一个新蒸出的白馍夹上刚炸出的藕盒子,顺嘴一咬,年味便弥散在了乡村的胡同和街道上。
年味,是一张岁月的红请帖,在辞旧迎新中让人不断成长;年味,是藏在记忆中最深沉的乡愁,在如水的年华里愈久愈醇厚;年味,是我们怀旧的情怀和对未来的美好日子的憧憬,它永远充满着家的欢笑和人间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