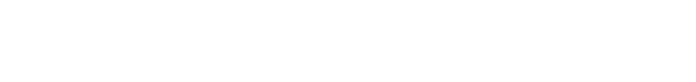张全华
父亲离世已三年有余,端详照片上的父亲,和蔼又威严,仿佛就在左右。我是家中的老幺,同时也是母亲常说的,是他这辈子懂得疼孩、最幸运的一个。
记得那是1978年,我跟着父亲在高庄中心校上小学三年级,父亲在校当校长,记得那时父亲总有开不完的会,忙不完的事。我在父亲一间被各种书籍和资料塞得满满的卧室里写作业。冬天天寒地冻,屋里也没有什么取暖设备,晚上冷得实在受不了,就使劲搓搓手、来来回回跺跺脚。记得一次下雪,父亲回来得特别晚,我又饿又怕不敢独自睡觉。待他回来已是一个雪人,我赶忙给父亲拍掉身上的雪倒了杯热水,父亲愧疚地说:“到一位父亲有病失学女生的家里,学校同意免除学费,劝其家长让她继续上学,耽误了一会儿。”我又饿又困赶快上了床。父亲说:“你的作业让我看看”,一边说着一边在一个放满衣服被褥的柜子里,颤颤巍巍拿出一个圆圆的东西,放在瓷缸里用热水泡上。我听着父亲对我作业的点评,说我写得不错,心里美滋滋的,这时才看清父亲原来烫的是一个皱巴巴又黄腾腾的苹果,漂在缸子里直打转。那个年代,苹果一年到头很难见到,更别说寒冬腊月天,父亲奖赏给我吃。
父亲在我们姊妹四个眼里既高大,又威严,一般不敢高声对他说话。我长这么大,父亲打过我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记得那时我四五岁,当时父亲在外地教书,周末才回家帮着干农活和家务事。家里有个猪圈常年养头母猪,是供我们姊妹上学的重要经济支柱。每每需要到外面铲一些杂草、干土(我们当地人称粪超)垫圈,同时又能在猪圈里积些土杂肥用来肥田。一个人用地排车拉粪超,车把放地上装不多,父亲一回来就让我帮着去扶车把。当时年龄小,我说走村西芦苇坑的近路快,不曾想在过芦苇坑时水湿了半截棉裤腿,本身看见父亲就胆怯,弄湿了半截裤腿怕挨训终究没敢去。父亲左等右等半天不见我,只好拉半车粪超赶回家。见我二话没说,一脚就把我跺出两三米开外,母亲怒斥父亲说孩子还小下如此狠手,要落下残疾就同父亲拼命。这事让我铭记终生,“无论大事小情都要勇于直面应对,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
父亲退休后的工资,完全可以照顾母亲和当时仍在上大学的我,可家里还有大嫂和几个侄子的六七亩耕地需要耕种。当了一辈子校长的父亲转身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无论春耕,还是秋收,无论在田间,还是在场院,父亲总是能够成为农事一把好手。
父亲退休后,我几乎没见他穿过新衣。父亲住在农村老家里,在地里干活不说,就是在家里修理农具、打扫庭院,总是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汗津津的旧衣服。姐姐心细,总是给父亲母亲购置一些新衣,可我发现除了春节和外出,从未见父亲穿过。母亲总是说:“你爹这辈子勤俭、小气惯了,钱更是舍不得花,可他对别人恳求帮忙的事,可大方了!”听村里的人说,父亲不管谁家大灾小难,即便是应急农时,总是二话不说,倾囊相助;至于别人还不还,母亲说爹从不放在心上,至于登门讨债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父亲也总常对我说:“谁没个难处,能帮一把是一把,应该的。”
父亲离我去了,可父亲的影子总伴我左右,父亲的音容总让我魂牵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