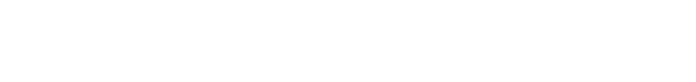徐善景
一场春雨过后,田里的麦子甩着腰身,开始疯长,跌入四月,就超过膝盖那么高。与麦子一样高的还有杂草,猪殃殃、野蒿、野燕麦……有的草,长得比麦子还高。
这个时候,娘的身影就出现在了麦田里。
弯身,捏住草的根部,薅掉。起身,把草抽出麦丛,搭在左边胳膊上。再弯身,再薅草……一个动作,来回重复,娘从早干到晚,不知做了多少次。地垄不算太长,娘把了四行麦,从地头,到地尾,胳膊上的杂草一大摞。一天下来,地头地尾堆起的杂草,像小山。
家里人口多,耕地也多,但能干活的劳力却不多。娘要为一家老小洗衣做饭,还要操心地里的活儿,特别是东洼和南地的两大块麦田,每块都有三亩多。娘说,麦是主粮,马虎不得。
娘的话是有原因的。那时,农村才刚解决温饱。几亩麦子,是全家人逢年过节能吃上白馍的保证,也是一家人的“钱袋子”。麦子收完晒干,交公粮一部分,变卖一部分,留下用于生活的,不足三分之一。因此,想着法儿让麦子增产,是娘最为关心的大事。麦田除草,只是娘关心麦子一项,娘说,再累,也不能让草跟麦子争肥。
杂草真多。开春时,娘已锄了一遍麦子,麦行间的杂草被消灭了,但跟麦子混长在一起的杂草是锄不掉的,只能等麦子起身长高了,才能一株一株薅。于是,每年四月里,娘每天都迎着朝阳,走进麦田,踏着晚霞,回到家中。她那早已不再挺拔的身姿,被阳光拉长,压短,演绎成麦田里的一道风景。
那天,娘在麦田里薅了一天草,晚上到家倒头就睡下了。娘只说有点累,一家人也没多在意。可第二天,娘起床做早饭时,感觉左脸麻木,左边身子也不舒服。我们看娘时,才发现娘的嘴歪在了左边。全家人都慌了,赶紧叫了村里的医生。
娘中风了!是在麦田不停地弯腰直腰,劳累成疾的。医生开了一大堆中药,要娘好好在家休息。可想想麦田里的杂草,娘没有心思歇,第二天就又出现在麦田里。
也就是从那一年起,娘的身体每况愈下,虽然第一次中风治疗及时,但时隔不久,娘便再一次病倒,之后又先后四次中风偏瘫,刚过六旬,便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娘憨了。但憨了的娘却始终惦记着麦田,趁家人不注意,就会挪着步子,走出家门,走出小巷,要去看麦子。可出了小巷,却找不到出村的路,返回又找不到回家的路。
娘憨了。但憨了的娘虽然记不起很多人的面孔,却时刻把她疼爱的小儿子记在心上。每当我从城里回家看娘,老远她都能认出来,就算我悄悄走到她身后,捂着她的眼睛,变着腔调问她我是谁,娘总能肯定地回答:“三儿,你是俺的老三儿!”
1998年的春天来得太晚了,进入农历二月,又下了一场大雪。那场大雪,造成气温骤降,娘,突然就走了。我拉着娘的手,哭得撕心裂肺,却怎么也唤不醒沉睡中的娘。
我们把娘埋在了麦子已经膝盖高的麦田里。娘“二七”那天正好清明节,我们去上坟时,天下起了细雨。我想,那一定是老天在流泪。
这几日,娘的身影总在眼前晃。想娘了!清明,再忙我也要回家,我要回去看看麦田里的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