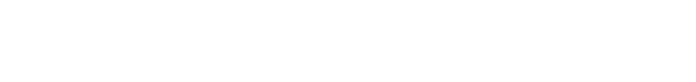孔金泉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记忆都封藏在胃里,春节也就成了一年中最大的慰藉。
“君子远庖厨”,我做不到,看着大人磨刀霍霍,我也跃跃欲试。养了一年的公鸡不再引吭高歌,从父亲生疏了一年的连贯动作,它应该能够解读出来一点什么,不再趾高气扬。脖颈上的毛被清理干净,然后一刀封喉,血咕咕冒出来,又像是它发出的最后的呢喃。择毛归我,热水浇淋,鸡毛就会应声脱落。我却无法耐着性子把绒毛一一去除干净,只能在父亲的嗔怪中一次次返工。
其实,我趋之若鹜的是烧锅,炉膛熊熊,什么都会在它的饕餮大嘴中被吞噬掉,火舌翻卷,好像里面有一只舞动的火凤凰。随着锅盖被蒸汽顶开,我的胃也躁动起来,藏着一只小鹿。母亲用筷子插一块肉,让我尝尝熟了没有。我顾不得淋漓的油汁就往嘴里塞,肉香扑鼻。“熟了,熟了。”“欠点火候。”“再加一点盐。”好像我是一个专业的品菜师,可以定论。我知道,那是妈妈在喂我肚子里的馋虫。因为,这些肉都是春节待客用的,煮完以后,就束之高阁了。
等炉膛暗下来,我会把红薯丢进去,用灰埋上。待红薯的甜香冒出来,再扒出来,大快朵颐。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耐住性子,扒得早了,红薯会被“气死”,再也烤不熟了。烤红薯要趁热吃,热与甜相互加持会让味道翻倍。吃完红薯,我成了李逵脸,抹得哪儿都是。母亲会笑得浑身乱颤,像个少女。
菏泽的风俗,春节当天会给长辈送一碗菜,我总是自告奋勇。一则,这碗菜上面会趴几块肥肉,让人垂涎,没人看见我就可以揩一点油。再则,长辈见我,总要抓一把瓜子糖什么的塞到我的兜里,满满当当。记忆中,那些胡同都被拉长如烟,有时我的嘴没有擦干净,还油光光的,母亲就会嗔怒地戳一下我的额头,“你呀!”努努嘴,意思别让我的父亲看见。
最让我乐此不疲的就是走亲戚了,远道的骑自行车,我坐在单杠上,警惕被父亲顶到屁股。近道的,就安步当车。其实是把自行车当驴马,怕累着。到了亲戚家就是客,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我总是吃得肚子滚圆。回来的路上,母亲说我没大猴,意思是没出息。我嘴上没说,肚子里反驳,饿着肚子就有出息了。记忆犹新的一次,我们去看一个长辈,长辈家似乎不想留饭,知趣的父母要走,我却闹着留下来。长辈磨不下面子,炒了几个菜。其中一个炒鸡蛋,掺了很多面粉,把鸡蛋的味道夺走了。回来的路上,父母狠狠批评了我,说他家里遭了灾,捉襟见肘,难啊!
现在我吃喝不愁了,却常常怀念少年的我,并在逆向增值中体味着那时无法言说的幸福。因为那时,我覆压大地的故乡在,我的爷爷奶奶在,爸爸妈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