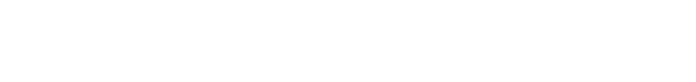易 文
一个时代的悲剧,不在于它没有英雄,而在于视英雄如草芥,让英雄蒙上悲情。
——题记
四百七十多年前,一个除夕之夜。
驻扎于陕北的明朝边防军突然出动。
将士们披坚执锐,顶着凛冽的寒风往北行进,去寻找那来去如风、难见踪影的蒙古骑兵,并力争将他们击溃。
这可是除夕之夜,天亮就是新年了。且不说大家打了一年仗,也该歇歇了,只说这蒙古骑兵,来无踪去无影,行动如风驰电掣,又上哪里去找?
但这支队伍的指挥官却坚定得很,他要求大家尽量悄无声息、全速前进。不久,他又要求全军像网一样撒开。等到收网,一支蒙古骑兵已经被一网打尽。这些蒙古兵面对神兵天降的大明军队还一脸懵——你们不是在忙着过年吗?怎么来到大漠里包了我们的“饺子”?
出发前满心疑虑的明军将士,至此时无不一身冷汗:要不是我们主动出击,还不被敌人包了“饺子”。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返回的路上,大家还在发问:是谁料事如神,知道敌人就在附近?
坐在马上的那位丰神俊逸的年轻指挥官语惊四座:“诸位没有看见傍晚时分西北方向有许多乌鸦麻雀蹊跷地飞起来吗?敌人已在近前啊。”
这位风度气质不俗的指挥官,就是时任大明兵部侍郎、总制三边军事、大名鼎鼎的曾铣(音同“洗”)!
在明代的一众牛人中,曾铣对后世人而言绝对是缺乏存在感的一个,甚至于他的名字都常常被人念错。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三十多年,却似一道闪电划破天际,令人惊艳。他少年时即有才名,二十多岁即考中进士,历知县、监察御史、辽东巡按、大理寺丞、右佥都御史、兵部侍郎、三边总制等职。巡抚山东时主持重修临清城,兴办教育;巡抚山西政声亦颇佳。辽东发生兵变,朝廷派他前往平叛,他采用分化、安抚、镇压等各种手段,很快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局势。
他离我们很远,但他的行迹却离我们很近——曲阜孔庙门口的太和元气坊我们都瞻仰过,那苍劲有力的“太和元气”四个大字,就是曾铣的手笔。
话题再回到曾铣的抗蒙事业。
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积极备战,完善边备,数次打退南下的蒙古骑兵,还利用蒙古人后方空虚的机会直捣其老巢。他还在实战中改进武器和战法,发明了“地雷”,创制了“慢炮”,一段时间蒙古人不敢与其交战。与蒙古人打交道多了,曾铣越来越感到河套地区的重要。河套地区即今天的宁夏及内蒙古鄂尔多斯、巴彦淖尔一带,也即黄河最北面几字湾内的那片富饶之地,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这片地方明初时一直为明朝所控制,但明中叶以后,随着边备松弛、明军战斗力下降,蒙古人逐渐向南占领了这一带,河套地区渐渐成了蒙古骑兵南下抢掠的基地。而失去河套地区的明朝再也没有了缓冲,腹地即暴露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蒙古骑兵来去自如,河套民众生灵涂炭,内地百姓亦是民不聊生。
胡虏肆虐、国无宁日,百姓在敌人的屠刀下呻吟,刚直不阿、立志报国的曾铣坐不住了。
正值盛年的他立志要报效国家、造福百姓。于是,他奋笔疾书,上书朝廷和皇帝,发誓要收复河套。
嘉靖皇帝一看很高兴:真能收复河套,自己的功劳可以和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相比了。当即准奏,并拨银20万两用于“复套”启动资金。内阁首辅夏言也大力支持,事情向着曾铣预想的目标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