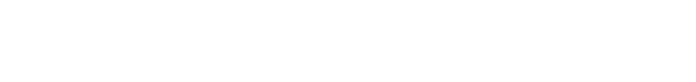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 孔庆贵
下火车,坐汽车。从济宁到菏泽的公路上,我望着郊外辽阔的田野上绿油油的禾苗,惊奇地问了母亲一句“这地里咋长那么多韭菜呀?”母亲带着疲惫忧郁的眼神,转头看向我,还是忍不住地被我的问话给逗笑了。母亲告诉我,“傻孩子,这哪是韭菜呀,是麦苗。”可对于在东北林区生活十六年的我来说,天天见山见水见森林,哪里见过这么多麦苗呀!我默默地记在了心里,绝不能再出现类似的笑话。
在火车上颠簸了三天两夜,亲人离别的忧伤,让母亲的心里承受了太多的牵挂与不舍,犹如汹涌的波涛一次次撞击着礁石,撞击着母亲脆弱的心。母亲一路上用沉默和寡言抵抗着心中的巨浪,但呆滞的眼神里却无法掩饰她内心的彷徨与焦虑。我对麦苗和韭菜辨识的无知,让母亲难得笑了,我也笑了。
这是四十二年前我和母亲、妹妹、弟弟,还有我小姨、二姨姐,跟随我父亲的工作调动来菏泽这座城市时的难忘一幕。这一幕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挥之不去。
听父亲讲,当年他从山东梁山去东北、加入逃荒大军时,是跟着我二大爷和几位老乡一起爬上绿皮火车,风尘仆仆地去了人迹罕至的那片黑土地。那年他十六岁。
父亲没上过一天学,没有知识,没有豪言壮语,没有豪情壮志,没有太多的祈求,来到这片黑土地上,只知道能吃饱肚子就行,想法简单得很。没有太多想法的父亲干起活来很专注、很细心,跟着开拖拉机的师傅在广阔的黑土地上来回奔跑,耕犁着温饱的希望。父亲在农场开了4年拖拉机后,一次天赐的机遇,被农场推荐给了来招工的一家林区的木材加工厂,成为一名正式工人,吃上了国粮,又学起了电焊工种,脱去了农村人的身份,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父亲是在农场认识母亲的。父亲向林区木材加工厂申请了住房,在同事和老乡们的恭喜声中,和我母亲结为伉俪,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安乐窝。母亲也离开了那家农场,在父亲的工厂里干起了临时工,脏活累活都很尽力,毫无怨言地负重前行。
从我记事的时候,爷爷每年都从老家梁山来东北住上几个月,在我家和二大爷家轮流吃住。有一年爷爷返回梁山老家不久,四叔就发电报过来,说我爷爷得了重病,住进了梁山医院,情况危急。父亲和我二大爷一商量,决定由我父亲回老家照顾病重的爷爷。在医院陪护肠肿瘤手术的爷爷一个多月,父亲都是睡在地铺上,三更五点地悉心照料,让爷爷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也让爷爷对父亲的孝心有了一种莫名的依赖感,不愿父亲离他而去。
没过多久,爷爷来信说,他病好后就去菏泽找了我奶奶的大侄子、我爸的表哥、我的表大爷,让他想办法把我们一家子调回梁山,也好方便照顾他和我奶奶。我的表大爷答应了我爷爷的请求。过了春节,爷爷没来东北,只是来信说我表大爷已经给我父亲联系好了单位,就等梁山发调动令了。可过了好几个月,父亲的单位却收到了菏泽发来的工作调动函,让父母感到有点意外,但毕竟还是回到山东老家。
这次举家迁移,我的母亲像离群的羔羊,默默地走向了几千公里外的平原山东,孤独、焦虑、不舍、无奈一齐涌上了母亲的心头。汽车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颠簸到傍晚才抵达菏泽汽车站。接站的是我的表大爷和表大娘。在去临时住所的路上,表大娘的一句“到喝汤时间了”,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喝汤”的菏泽方言。我在想,喝完汤,我便与菏泽结下了缘分,菏泽,从此也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