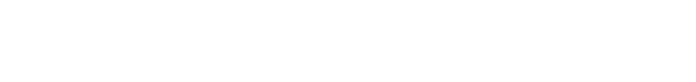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 平书宪
记忆深处,总有一缕带着柴火香的气息,穿透岁月的迷雾,将时光重新拉回鲁西南的农家小院。故乡酱豆子的味道是镌刻在味蕾上的永恒印记,它藏着母亲的温柔,裹着故乡的烟火,更串联起了岁月中无数个温暖的瞬间。
酱豆子是鲁西南农村流行的一种小吃,也是物资匮乏年代餐桌上的下饭主打菜,具有一种芳香浓郁的特殊味道。这种味道是人与微生物携手的成果,而这种手法则被称作“发酵”。做酱豆子一般就地取材,做法简单,但需要把握好发酵环境和温度,必须有经验才能够做好。
记得小时候母亲总说,做酱豆子要等老天爷赏脸。初冬季节某个晴好天气的上午,母亲将晒得发亮的黄豆倒进铁锅,清水漫过豆子的刹那间,仿佛听见时光汩汩流动的声音。柴火在灶膛里跳跃,映得母亲的脸庞忽明忽暗。她守在灶台前,不时掀开锅盖搅动,水蒸气模糊了鬓角的白发。当黄豆变得绵软,母亲才用粗布仔细地滤干水分,将它们小心翼翼地裹进新缝的棉布袋,埋进尚有余温的柴火灰里。等待发酵的日子,也成了我童年最神秘的期盼。我常蹲在灶台边,盯着那鼓起的布袋发呆,想象里面正在上演的奇妙魔法。母亲说这是与时间的约定,急不得。某个清晨,母亲忽然停下手中的活计,眼神里闪过欣喜:“该出锅了。”布袋解开的瞬间,浓烈的发酵气息扑面而来。年幼的我被熏得直捂鼻子,母亲却像捧着珍宝似的仔细查看,并用木勺挑起一把豆子,见银丝般的菌丝缠绕,才满意地笑着说:“成了!”
晾晒后的酱豆子与切碎的白菜、辣萝卜在陶缸里“相遇”,再撒上粗盐、姜片,就开始了漫长的融合。母亲总会在缸口蒙上蓝印花布,用竹篾扎紧,仿佛封存一个关于味道的秘密。半个月后,当母亲掀开缸盖的那一刻,浓郁的酱香味顿时弥漫整个院子。母亲盛了满满一大碗,小心地滴上几滴香油,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后,夹起来放进我的嘴里,咸香中带有醇厚的发酵味儿,真是越嚼越香。
初中住校的日子,酱豆子成了我最温暖的慰藉。每个周日傍晚,母亲都会把酱豆子装满玻璃瓶,用蜡油封住瓶口。清晨的教室里,掀开瓶盖的瞬间,熟悉的香气总会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我们围坐在宿舍的铁架床边,就着馒头分享酱豆子,苦涩的住校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记得某个寒冬,我发烧卧床,同宿舍的李合群将他仅存的半瓶酱豆子推给我说:“吃点咸的,出出汗就好了。”那带着体温的玻璃瓶,盛的不仅是酱豆子,更是年少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
考上县城高中后,回家的路变得漫长,每两个星期的周末成了最奢侈的期待。当我推开家门的瞬间,总能看见母亲系着褪色的蓝围裙,在灶台前翻炒酱豆子。铁锅与铲子碰撞出欢快的节奏,腊肉的油花溅进酱豆子里,发出滋滋的声响。母亲总说:“学校的饭菜哪比得上家里的养人!”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坐在一旁用围裙擦着手,眼神里盛满笑意,偶尔伸手替我擦掉嘴角的酱汁。那一刻,所有的思念与疲惫,都在这温暖的香气中消散。
从县城中学到省城大学,再到定居都市,我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奔忙,日子被切割成忙碌的碎片,返乡的次数屈指可数。去年春节假期,我到大舅家拜年,刚进院子,一股熟悉的香气便勾住了脚步。我循着香味走进厨房,只见舅妈正在翻炒腊肉酱豆,铁锅里的酱豆子裹着油光,腾起的热气中满是童年的记忆。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熟悉的味道瞬间击溃了所有的伪装,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舅妈笑着说:“你娘才是做酱豆子的行家,俺这手艺还是跟她学的哩!”母亲站在一旁,眼角笑出细密的皱纹:“俺家这孩子,走到哪儿都忘不了这口啊!”
返程那天,母亲悄悄往我的车后备箱塞满了土特产。回到家后,打开车后备箱,贴着红纸条的两瓶酱豆子映入眼帘,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给娃的”。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她的声音带着笑意说:“这是跟你舅妈要的酱豆子,让你尝尝鲜。以后再想吃的时候跟娘说,娘给你做!”正月十五刚过,母亲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手里提着用旧棉袄裹着的塑料袋,打开一看是新鲜的酱豆子,还带着余温。那一刻,我所有的思念与牵挂都化作了夺眶而出的泪水。
如今,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酱菜难以勾起我的食欲,而那坛带着柴火味的酱豆子,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成为我心中永不熄灭的灯火,照亮着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