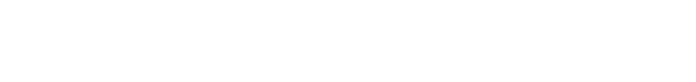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 李俊明
前几日,在东明县博物馆“黄河民俗展厅”,我看见了一间老堂屋客厅的布局摆设,恍若重回旧时光。
老瓦房,长辈的堂屋客厅里,一张老式长条几两头翘起。条几前,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北墙上,正对堂屋门挂着中堂画,画的是一条鲤鱼,在汹涌波涛之上,摇头摆尾,有鲤鱼跳龙门的意境。中堂画两边,配着对联。
目睹此情此景,我恍然觉得,它就是我家的老堂屋。
据我爹讲,1943年到1954年,在城里中心地带——大隅首北路东,我家里开着荣茂祥百货店。全家住在店铺后宅里的时候,因为生意兴隆,家境逐步殷实,我老爷爷住的堂屋正中间,就有这样的摆设。
老爷爷去世后,我爷爷成了家族里的掌门。他和我奶奶住的堂屋正中间的一间房也摆上了长条几、八仙桌。椅子,不是太师椅,而是老式圈椅。正对门口的墙上,挂着中堂画。春节期间,中堂画换成轴子——大型家庭族谱。那时候,爷爷的堂屋是家族人聚会的场所,是街坊邻居串门拉家常的场所,也是春节期间拜祭祖先的庄重之地。
年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中午,将八仙桌往前拉,周围摆上椅子和条凳,全家人聚餐。那时候,生活艰难,平时吃饱肚子都成问题。可是,每到春节,八仙桌上总要摆上荤素搭配的菜肴。家族里的成年男人,围坐一起,吃菜喝酒谈天说地,其乐融融。小孩子和妇女坐在一旁,吃吃喝喝,说说笑笑,打牙祭,也吃几顿饱饭,让平时瘪瘪的肚子撑得鼓鼓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刮起了“破四旧”的飓风,我爷爷堂屋里的中堂画和轴子刮没了。
爷爷奶奶不在了,我爹成了家里的掌门。20世纪80年代,他和我娘住的堂屋明间也摆上了长条几、八仙桌。长条几,是我二哥找木匠按明代风格制作的。八仙桌,是我爷爷屋里的老物件。看模样,就知道有年头了,像是明代风格,榫木结构,造型简洁朴素。老式圈椅,也像明代风格,线条流畅,比例匀称,简约大方。掂一掂,分量很足,应该是好木头做的。深棕色,带包浆,摸一摸扶手,滑润润的。一位木匠说,“论年龄,肯定比你爹大。”他这一说,那把椅子至少得有“上百岁”,也许就是明清时期制作的。一开始,只有一把。后来,我爹又在集市上淘来一把。也巧了,和家里的老式圈椅一模一样。破损的地方,找木匠修了修,凑够了两把。中堂画和对联本是印刷品,印着一只大老虎,时间长了,破损了。轴子,也破旧不堪。21世纪初,我让人把一个大学美术教授赠我的一幅鲜花盛开的国画裱成中堂画,又自己动笔写了一副对联,也裱了。崭新的中堂画和对联让屋子光亮了许多。我爹让我一个表哥精心制作了一幅新轴子。新轴子最顶端画着祠堂建筑,下面是层层分级的牌位图,写着一代代先祖的姓名,一看就清晰明白。春节时,悬挂新轴子,轴子下面的条几上摆上爷爷奶奶的牌位,八仙桌上,摆满供品,供奉祖先。
平时,我爹的亲弟弟堂弟弟,还有要好的街坊邻居,曾经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老同事经常来串门。倘若来人是一位,我爹和客人就一人坐一把老式圈椅。人多了,再分坐在两侧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谈笑风生。
每逢春节,从天色微明到中午十二点,家族人、街坊邻居前来拜年,络绎不绝。我爹娘分坐在老式圈椅上,笑盈盈地迎送客人,接受晚辈跪拜。条几和八仙桌上,摆满了水果糖和点心,还有花生核桃和瓜子。来人了,爹娘就催着来人吃。小孩子来了,还会捧上一把,递到他们手里。大人来了,我爹送上一杯热茶,让客人满嘴沁香,又暖心润肺。
中午吃饭时,八仙桌变成餐桌,一家三代人,后来是四代人,荤荤素素,推杯换盏,快乐无穷。吃过午饭,将八仙桌往前移动,就成了麻将桌。我们这一辈人,围坐在一起打麻将。老爹和老娘坐在麻将桌旁边的沙发上,笑盈盈地看着我们打。偶尔,老爹还会喊一嗓子:“三儿,打八条!”“美菊,你咋不碰啊?”
这样的场景,腊月二十三就开始了。腊月二十三是我爹的生日,一家人聚在一起,为老爹祝寿。一直到正月十六,才告一段落。正月十六,闺女回娘家,是一家人的团圆日。
我爹娘的堂屋,人来人往,笑声不断,热闹非凡。家庭和睦幸福的气氛经常洋溢在堂屋里。血缘亲情在那座屋子里浓得化不开。
我娘和爹先后离世。那座堂屋,连带里面的家具摆设都归了二哥。不久,赶上城市拆迁。老房子没了,堂屋,连带条几八仙桌中堂画都没有了。我也没打听究竟去了何处。现在想想,甚觉可惜。唯有轴子被我二哥带到新楼房里,春节期间挂一挂,以表对先祖的怀念。然而,大年初一络绎不绝串门拜年的人越来越少,最近两年,几乎没有了。
老胡同,旧庭院,被一栋栋高楼取代,老式民宅,堂屋客厅连带里面的所有旧摆设,也随之一一消失。传统家庭模式在物化变迁中流于记忆。老风俗习惯、家族血缘亲情、邻里友情,一应传统文化精神的沿袭也随之逐渐淡化。
沧海桑田,瞬息万变,我们接受不接受,它都在变。还是随缘随分、与时偕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