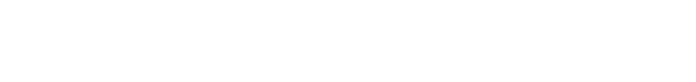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 郭晓兰
父亲站在悠远、辽阔的旷野,本身就是一株麦子。在攒足了热情的阳光下,在麦香成熟的夏风里,父亲一遍一遍弯腰挥镰与麦子、土地对话的声音,和着人欢马叫、牛哞鸟鸣的声音,汇成一首热腾腾粗犷浑厚的命运交响曲。父亲试图将他对世界的理解描画成一个个四方图形,里面是一方方他可以掌控的厚重的土地,只要他肯弯腰垂首流汗,就可以靠生命的力量挥洒成一幅乡村的水墨丹青,大豆青青,高粱锈红,玉米亮黄,麦穗缀金。
站满麦穗的田野,可是父亲用毕生的汗水与深情打造的一部作品,年复一年栉风沐雨,春华秋实。父亲从他的韶华青青开始,带领他手下的乡亲为了手中饭碗的丰富充实而呕心沥血,不辞劳苦。从我记事起,我们的生产小队是村里,不,是三个村十二个小队中最富裕最令人羡慕的一个,也是全乡镇最闻名的一个。父亲让人开辟了桃行、苹果行、瓜行、杏林,让懂技术的队员和孤苦无依的老人来管理,工分双倍另计。到了收获季节,家家喜气洋洋,瓜果一堆一堆的排列成行,孩子们在果林里兴奋得跑来蹿去,等待领取分享。更有一次分口粮的场景一直镌刻并且照亮在生命的天空:乡亲们拿着大大小小的粗布粮袋,喜气洋洋地在打麦场里聚集,等待领取96斤小麦口粮,同时大声地谈论着其它村队乡亲的情况。有的是用碗计量分配的,有的是几斤,还有一个根本没动杆秤。那爽朗骄傲的笑声惊飞了天上的鸟儿,惊破了天上的云儿,一直萦绕在我的梦里。在麦秸垛上爬来爬去戏耍的我当时纳闷得很,没用动秤什么意思呢,也用碗量的吗,还是用盆子量的呢,或者干脆一袋一袋扛回家呢?或者根本就什么也没分到呢?
后来,等到其它小队分到96斤这个令人欢喜的数字时,父亲带领的乡亲每家每户收入已经到了三四千斤或者四五千斤。父亲用他那颗善良智慧的头脑,带领乡亲们早早地秘密地实行了承包责任制,乡亲们积极性空前提高,又都守口如瓶。这是政策实行之前公开的“秘密”和“错误”,大家能填饱肚子,自然齐力齐心,上级很多次的检查或调查在父亲的调配下都巧妙地安然无恙,安然无恙中充溢着令大家心里没底的极度惊险和事过情迁对父亲的心服口服。那年月,我们的生产队交公粮交得多、吃得饱、还能稍有富余接济亲邻,身为父亲带领的队员,脸上的骄傲和笑容是最多的,笑声是最爽朗的,烟火柴米气里是最硬气的。腰板硬气,说话硬气,在亲戚邻居面前硬气。
父亲一干就是几十年。没入曙色的天上的星光记得父亲匆匆出行的脚步;没入夜色的地上的灯光记得父亲疲惫归来的身影,父亲属于每一块庄稼的土地,属于庄稼地里信赖他的乡亲们。父亲对他掌控的几百亩土地的熟悉,远胜过他的儿女,他对它们的大小厚薄肥瘦脾性了如指掌,对儿女的高矮胖瘦性格心绪却浑然不知,他只关心,我们双手虔诚捧着的碗盏里,盛的是能映照人影的稀水饭汤还是能让我们长身体的结实食粮。他奔走在土地与土地、土地与乡亲们之间,家似乎只是他权做栖息的客店一般。极度忙碌的母亲的埋怨,回响着父亲忘我付出的艰辛;眼巴巴盼着天落雨留住父亲想偎依一下的我们,记得父亲的辛劳。
我们在父亲耕耘的天空下终究是一株不安分的麦穗,最终离开那片深厚的土地,扎根在熙熙攘攘的小城努力行走与耕耘。父亲习惯带着他汗水浸泡的麦子,或亲手打磨的麦面,或种植的蔬菜来小城,他要将故乡温暖的太阳带给我们,将村庄宁谧的月光摘给我们,让我们即使离开了土地,也仍拥有一份土地的宽厚、踏实、从容与安详。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无数光阴挂在垄头麦芒的微光里,苍老的父亲立在岁月的堤坝,把自己最终长成一株沉甸甸的麦穗,向大地和尘世进献他的一份人生的虔诚和硬朗,也将人性的良善、质朴、忠厚和感恩种植在我们的骨头里。父亲是生长在我意志和灵魂里青翠的春天,暖风一吹,心底的麦子伸茎长叶,抽穗扬花,结实灌浆,瞬间铺满麦穗饱满的金黄,骨骼与麦秆之间弹奏的,自是一曲几千年来长盛不衰、悦耳动听的清脆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