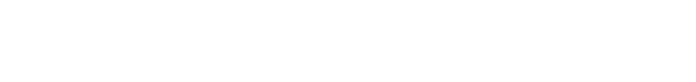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 刘永华
天气渐寒,超市里的人气愈发高涨了。望着长长的保鲜柜里摆放整齐的五花肉、精瘦肉、肋排等,忽然想起我年幼时买肉的一些事来。
“明儿个星期天,你和你二哥去王屯集上割斤肉吧,快到八月十五了,家里连个油星也没有。”“中,娘!”姐姐和二哥刚从学校回来放下书包,一听说去集上割肉,高兴地连忙答应。“娘,我也去!”“去吧,省得在家闹心我。”那年,我五岁了。
五十年前的农村,每到初冬季节,生产队里会分给每户社员一些棉花,每家再把轧棉花时轧出的棉花籽拿到油坊榨出几斤棉籽油来,俗称“棉油”。母亲总是把油罐子放在厨屋里,用麻绳子高高吊起来预防老鼠偷吃。就是这几斤棉油,在那个困苦岁月里,是每户农民家庭一年里最奢侈最有营养的食品了。
“就可着这些钱割肉。”第二天刚吃了早饭,娘从手巾卷里小心捏出一块钱来交给姐姐,姐姐和二哥就带着我上路了。
虎子(家里喂的一只棕黄色的土狗)的肚子就像被抽了真空似的总是瘪着,在前面跑着撒欢。王屯集其实是“王浩屯集”,都习惯叫“王屯集”,集市离俺家郭鲁村子足足有八里多的路程。姐姐挎着个平时割草用的柳编篮子,走路时间长了胳臂就勒得疼,终于和二哥说好轮换着每人挎一里地。我只是在后面跟着走,有时是小跑。
王屯集上的食品站门朝北,院子里一个木头架子上吊着两扇白花花的猪肉扇子。一黝黑的中年男子一边咿咿呀呀哼唱着不知名的小曲儿,一边挥着白刺刺的刀切割着猪肉。来割肉的人很少,“你割几斤?”“就可着这一块钱割吧。”姐姐怯怯地说。但见他用刀轻轻划了一下,把这块白白长长的肉块称了:“一斤七两,正好!”姐姐就像捡了一个宝贝,慌忙把肉放在篮子里,忙招呼着我和二哥回家了。
“二哥,这块肉一点瘦的也没有,都成白油了,到家娘又吵咱!”姐姐揪心地和二哥说着话。虎子似乎闻到了肉香,愈发撒欢跑在我们头里,竟不知不觉到家了。
“恁几个怪能哩,割的这块肥肉真好,一会儿炼些猪油,八月十五咱就有油吃了!”娘一边夸赞着一边摸着我的头,“饿了吧,走时忘了给些零钱了,也没钱在集上买个馍吃!”姐姐看到娘高兴的样子,居然没有因为肉太肥而挨吵,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二哥偷懒,他早躺床上看书去了。厨屋里又熏又脏的烧锅活儿自然又是姐姐的了。娘把洗净切成块的肥肉放入锅里,那白嫩的猪肉块与炽热的铁锅接触的一刹那,“刺刺啦啦”地响并冒起喷香的烟雾来。娘眯缝着眼睛,用铲子不停地按压着肉块,想让它尽可能地多挤出几滴油来,肉块由白渐渐地变成黄色的了。“看把小三儿馋的。”娘边说边把一块黄色的“油滋啦”塞到我嘴里。我竟不怕烫,只嚼了下就吞下肚了,只觉着香。
姐姐把存放在她床底下好长时间的一个大冬瓜抱出来打皮切块,中午美美地吃了一顿“油滋啦炒冬瓜”。“娘,这菜真香!”看着我和姐姐哥哥们狼吞虎咽吃饭的样子,娘的眼睛突然湿润了:“等到过年你爹回来咱多割斤肉吃!”边说边把她碗里仅有的一块“油滋啦”用筷子夹到我碗里。
“您好,请称一块肥些的肉,回家炼油!”我对站在柜台后面忙着整理肉品的姑娘说。是啊,有那么些年再没有吃到“油滋啦炖冬瓜”那样的美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