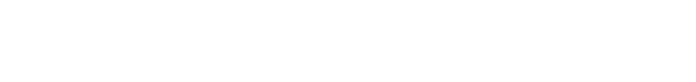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 姜宝凤
又到冬季,望着窗外寒风萧萧的天气,不由自主想起当年祖母为我缝制棉鞋的情景,顿时一股暖流冲破记忆的闸门涌向心尖,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那时生活物资极度匮乏,老百姓家的日子普遍非常贫穷。仅从吃穿用上说,吃的是“瓜菜半年粮”;穿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用的东西基本上凭票购买,有些物品还限量供应,不是你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所以从记事起,生活的苦难就像一条毒蛇,啃噬着我幼小的心灵。即便如此,令我引以为豪且难以忘怀的是,在每年漫长的冬天里,我都能穿上一双由祖母亲手一针一线为我缝制的新棉鞋。至少,年年冬天穿着合脚的棉鞋,我不会像周围的小伙伴那样几乎个个脚上生冻疮,红肿红肿的,就跟夏天吃的水萝卜一样,痛痒难忍。
那些年,人们很少舍得花钱买鞋穿,穿的几乎都是手工做的布鞋,空闲时家庭妇女们就开始张罗着做布鞋了。对一般的妇女来说,普通的布鞋好做,但做起棉鞋来可就有一些费事了。祖母的针线活儿在村里是有口皆碑的,平素里常见她戴着老花镜打个补丁缝个裂口什么的,细细的钢针在她手里翻来覆去、轻松自如,针脚不冒线不走形,在村里无不被人羡慕。
那时,左邻右舍有结婚或出嫁的小伙子大姑娘绣床单、被面、花枕头等嫁妆都争相来请我祖母;村里过百岁的小娃娃需穿虎头鞋、戴虎头帽,也必得由我祖母做;逢年过节剪裁个男女老少各款式衣服,祖母照样拿得起放得下。
祖母做什么样的鞋就先用报纸或旧书本剪什么样的鞋样,鞋子做得多了,光样式各异、型号不一的鞋样就夹满了好几本大厚书,连火炕的草席底下都压了一两层。做一双鞋子无论是单鞋还是棉鞋,基本上分三步:打布壳、纳鞋底、上鞋帮,一步步做成要耗费许多时日。
当时,家里实在不能穿的破烂衣物和不能用的剩布头,在祖母眼里就成了宝贝,她经常手抄剪子,把有用的布片剪下来,农村人把这些布片子称为“铺衬”。待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就取来门板或饭桌,铺在上面用面粉和成浆糊,把布片一层层展平对接粘起来,晒干后硬如纸壳,再照着鞋样把打好的布壳裁剪成鞋底和鞋帮的形状。接下来,纳鞋底之前,要先将一张张鞋底壳均匀地叠加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地方叫“千层底”的原因,叠到一定厚度时用崭新的白棉布上下盖面,左右封边,然后就可以纳鞋底了。
纳鞋底用的大都是粗麻线,每纳一针得先用锥子扎一个孔,后用套在中指上的铜顶针一顶把针线穿过去,再使劲儿地拽几下,偶尔祖母把针快速地在发髻上划一下,为的是走针时更顺滑,再如此反复纳下一针,那密密麻麻的针脚就留在鞋底上了。针脚的大小决定做出的鞋底是否结实耐磨,所以需要千针万线才能纳成一双鞋底,那针脚一行行,一排排,十分整齐,透出一种娴熟、优雅之美。纳鞋底是个劳神费力的慢功夫苦活,时间一长,祖母的手指会酸痛,眼睛会发花,有时祖母还不小心会扎着手指,放在嘴里去吮吸,每次看见,我都十分心疼。因此,在小时候的无数个夜里,我是经常望着祖母在昏暗的油灯下神情专注的背影和听着麻线抽动的嗤嗤声渐渐地进入梦乡的。
纳好鞋底,接着就是上鞋帮,鞋帮和脚面是一体的,成倒“几”字形。如果是棉鞋,鞋帮里面要夯上棉絮,内贴绒布。上鞋帮也是个技术活,没个好手艺,鞋帮就会上偏,穿着难看还不舒服。因此,祖母将穿了细麻线的钢针从上往下,把鞋帮和鞋底一起穿透,每上一针都要仔细比量一下歪正,然后用力拉紧针线,鞋帮就被紧紧地上在鞋底上。祖母做鞋的细心和耐心是出了名的,她做出的鞋不仅穿着舒服,而且特别美观,每次穿出去,人们都啧啧称赞。
我就是这样穿着祖母做的棉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数九寒冬,走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一晃40多年,如今祖母也早已驾鹤仙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怀念祖母为我做棉鞋的情景。每每回想,心里总有一种无法名状的隐痛,久久不能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