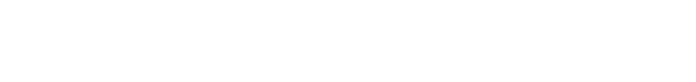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 陈 奇
如今,在我住房的楼梯间,还珍藏着30多年前大学毕业捎回来的4把暖壶。前些年,每逢节日卫生大扫除,妻子都会嘟囔:这些暖壶谁还用?一直放着它干啥?扔了呗。我总是慌忙制止:一定要放好,这壶里有故事。一见到它,我就似乎又能回到美好的大学时代。
那是我刚上大学时,早中晚三餐后,我基本上是掂着一壶水就向教室里赶。我们班有几位走读生,他们吃完饭就往学校赶,见我的课桌旁总是放着暖壶,因他们在家大都顾不上喝水,便自带水杯到我这里讨杯水喝。壶里水喝完了,我会跑下楼去,到锅炉房再掂一壶。老师走上讲台上课了,看到他们讲课讲得口干舌焦却喝不上口水,我心中不安起来:这怎么能行?学生听课还想喝口水呢,老师讲课更需要喝水呀!
下课后,我匆匆走进学校小卖部,又买了一把暖壶、水杯和档次高一些的茶叶。班主任魏凤娥老师再次走上讲台上课时,发现面前的讲课桌上,其绿油油的茶叶还在刚刚斟上热水的崭新水杯里上下沉浮,一把新暖壶也在讲课桌一旁的地面上放着。我看到她不由得先是一惊,接着两眼放光,轻轻摸了一下热乎乎的杯子,深情地望着全班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轻声说:“谢谢同学们,从这杯茶水我看到了你们对知识的渴求。”我虽坐在班里偏后位置,对眼前这感人的一幕,却看得真切,心里暖暖的。看到一些同学把赞许的目光投向我时,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魏老师讲了一阵子课,在让同学们看书阅读时,她不由自主地端起茶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茶,我觉得比自己喝了心里还甜。
后来,随着课程开得越来越多,讲课的老师也多起来了,经常性上课的就有八九位老师。我为老师们买的茶杯也从一两个逐渐增加到八九个。为防止老师们相互用错,我又一一贴上“X老师专用”的纸条。
由于为老师配的茶杯较多,我不得不加强管理。每一位老师下课离开教室后,我既要把他的杯子刷净放在桌橱里,而且还要按照课程表把应该上课老师的茶杯取出来,沏茶以待。如此循环往复,从不停息。这样,我们班级无论哪位老师走上讲台,都有浸满茶香、散发着热气的水杯在恭候着他。
再说同学们,在班空里喝水的人也越来越多。原来的两个暖壶,已远远不够师生们喝的。于是,我又买了两把暖壶。每次下楼提水两只手各提两壶,一口气上四楼,虽累得气喘吁吁,可觉得老师和同学们因我而喝上水,无口渴之忧,心里总是有说不出的高兴。
就这样,我慢慢地成为老师和同学们心目中的“义务茶水供应员”。可就在我走进大学才一个来月的一天傍晚,突然接到家里人打来的电话,说我的岳父不幸因病去世了。我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我是他老人家唯一的女婿,我立马向老师请了假,星夜启程。
当我千里迢迢从家归来,前后虽仅三天时间,可班里同学们见了我都说:“你这一请假可好了,同学们喝不上水事小,老师们在讲台上也看不到他们熟悉的写有自己名字的茶杯了。还有一位教文学理论的吴老师,他在其他班级讲课,讲得口渴了到我们班里来找水喝没喝上,当得知我请假回家了,吴老师喃喃地说,陈奇不在,水也就没了。”听同学们说到这里,我遗憾得身上直冒汗,都怨我走得太匆忙,没来得及安排其他同学代我尽供水之责。有了这一次教训,在整个大学期间,无论是酷暑盛夏,还是三九寒冬;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大雪纷飞,老师讲台上的水杯总是热茶满满。我手里的4把暖壶每一天都在掂上掂下,从没有停息过。
大学毕业时,我们班的班主任魏凤娥老师在离校的一队队、一群群毕业生中终于找到了我。一阵紧紧握手后,她让我从提包里找出人手一本的《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纪念册》,她掏出笔来,在册子里挥笔写下四个大字:堪称吾师!
如今,倏然30多年过去了,每每看到这4把暖壶,再摸摸那因长时间掂水而被磨得滑溜溜的把手,我似乎又回到了大学的课堂里: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又口渴了吧,我还想继续为您提水倒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