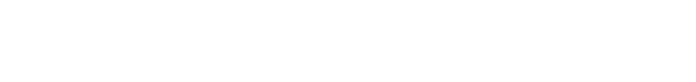出潼关
故乡有山有水,都是极普通的山水。山既不巍峨也不秀丽,水既不浩瀚也不清幽,却足以养育一代一代的家乡人。又因了生命最初的经历,它们始终在我内心深处存在着,一个坚定如父亲,一个柔谨如母亲,是我最深切的依恋。
回老家,即便只住一日,也要往村后的小山上去几次。山是石头山,土极稀薄,却已被柏树和果树密密地覆盖。小山没有名字,只有三十多米高,站在山顶仍足以俯瞰整个村庄。小时候,一座山便是我们的一个世界,各种植物和动物给我们许多乐趣。离开家后,才觉得小山更是成年人的世界,每一块石头都饱受风吹日晒,每一棵树、一株草都历经风吹雨打。在这里能感受到时间的重量,父亲的皱纹、母亲的白发不是一日生出的,我们追求的成功也必是经过几多摔打才能到来的。
秋天是草木最为葱茏的时节,那些野草像是蛰伏在地面很久,突然就爆发了一样,它们格外繁茂,野蛮地生长。上山的小路已经被两侧的野草侵占了,试着行走了几步,终究发现蹚不过去,只得作罢。
除了村后的小山,还有一处儿时的乐园,便是村西边的小河了。这条河也没有名字,距离村子有三里地远,中间是深远的田地。在我小的时候,一个孩子从小孩变成大孩,就是从跳下这条河游泳开始的。人一定有着亲水的本性,夏季来临,燥热让人无处躲藏,小河便成为最佳的去处。太小的孩子是不能也不敢下水的,十来岁的孩子才被默许可以下水。多数孩子只会狗刨和仰泳,狗刨是最常用的动作。因为不会换气,一个个紧闭着嘴,鼓涨着腮,双臂慌张地刨水,两腿拍打着水面,激起很高的水花。
这条南北走向的小河,究竟有多长,它又是哪一条河的支流,我们并不知道。从村子沿田间的土路一直向西,就到了小桥处。小桥并不是专门供人和车通行的桥,其上方是一个石头垒砌而成的漕渠,用来灌溉庄稼的。我们并不懂这些,统统叫它桥的。一个个光着屁股的孩子从水里走到桥上,依次往水里跳。跳的时候并不是头朝下,而是像跳崖一样地直着下去,水花溅得老高,整个人沉下去,不一会儿,一个黑黑的脑袋从水下浮上来。
这条河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当我们长大一些,再不好意思光着屁股下水,就逐渐告别这条小河了。河里是小孩子们的世界,没有人穿着裤头下水,那样显得比光屁股更骚包。在我离开家乡之后,很多年不曾来到这条小河边了。
这个秋天的傍晚,我骑着电动三轮车,穿过收获后的田野,专程来看它。一路上都是沉静的,空中不时有喜鹊和斑鸠飞过。三十年后,我再度站在漕渠上打量这条河,忽然想起我们当时叫这里“河沿儿”的。河的两侧是高高的土沿儿,上面长满树;沿儿的外侧就是田地,小河像是在摇篮里。
小的时候,站在这个位置,桥下悠悠的河水也让我看得沉迷。那水始终无声地向北涌动,水面上有细长的鲦鱼轻灵地游动,潇洒极了。我的目光常常在远处的水面游走,期望发现大一些的鱼浮上水面,却从来没有见到。如今,经历了夏日里急躁的降雨,河水无比丰盈,且又沉静。像山上的草木一样,河水恣意地流着,仿佛不是来自外界的降雨,而是从底下生出许多水来。
河面倒映了蓝天白云,越发显得澄澈,正是秋水共长天一色。难怪人们用秋水比喻女子的明眸,这样的眼睛不仅清澈,而且沉定,不妩媚,不刻薄,不慌张。
小河两岸,仍然生长着茂密的芦苇。这种古老的植物是《诗经·国风·秦风》中的蒹葭,并留下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佳句。那些茂密的、颀长的芦苇,深情地隔水相望,它们在风中摇曳,轻抚水面,似是风情万种。
秋天的小河接纳了夏天的雨水供给,又褪去了急躁喧嚣,变得丰盈而从容;它将流向一个寒冷的季节,在凛冽的风里瘦下去,变得刻板而僵硬。如此,在春天里萌动,在夏天里奔放,在秋天里丰盈,在冬天里衰老,小河的四季,如人的一生。
站在漕渠上,四下无声,小河如绿色的玉带一般向南北延伸着。我仿佛看到水中的少年嬉戏着,漕渠上的孩子猛地跳到水中,笑声与水花一起翻腾。
那一河秋水,最懂岁月不居,悠悠地涌动着。一枚树叶落在水上,似一叶小舟缓缓移动,载着我的童年和乡愁,飘向远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