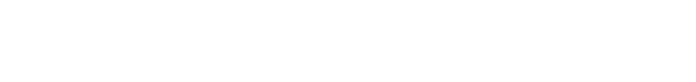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 孔伟建
(一)
当投递员将第24期《读者》杂志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知道2023年已接近尾声了。一年,化为堆放在我床头上的24期花花绿绿的《读者》杂志,再次翻阅,竟有今夕何夕之感。
连续多年了,似乎每年都是这样度过的。因为订阅了《读者》《散文》等杂志,我觉得日子被赋予了另外一层意义,我觉得我订阅的那些杂志带着文字的温度和遥远的问候始终走在路上,树叶一样稠密的日子就在我的期盼之中不觉流过。快,也是它。慢,也是它。
年终岁尾,当我看着自己一年来写下的那些文字、订阅的那些杂志、剪下的那些剪报之时,觉得一年的时光一下子被浓缩了,浓缩为一篇篇文章、一点点足迹、一行行文字。字里行间,岁月履痕,前尘旧事,遥不可及,又触手可及。
我慢慢地活着,慢慢地写作,在这条寂寞之道上自得其乐。人到中年,我越来越感觉到,在当今时代从容不迫是一种多么难以企及的境界。我记住了一些人,记住了一些事。也忘记了一些人,忘记了一些事。
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触动了很多人,其中也包括我。有时候,听着听着,泪就下来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生何其短暂,何况一年!
(二)
我已几年不用日历了,那种手撕的纸质日历。手机取代了一切,它将万年历和时间浓缩于股掌之间,跟我朝夕相伴。
朋友圈功能很强大,总有些好心人在某些时间节点提前提醒我,比如,每年岁末,各种感慨就会刷爆朋友圈。我被裹挟其间,知道年底到了。
要是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前,我还会想着给远方的朋友寄发张明信片或寄封信什么的,但现在不用了,手机微信取代了一切。
手机功能强大,语音、图片、视频,应有尽有。每每需要沉静时,手机往往会突然响起。可把手机关了,没电话来,心里却又感失落。通讯发达,带来生活便捷的同时,把我们的性格折磨成了什么模样?
(三)
岁末,我喜欢过周末,宅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就很好。
冬阳真好,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看会书,看看阳台上那几盆花,或放首歌听,周围很静,能看见细微的灰尘在阳光里浮动。
如出去,也不走远,就到楼前护城河边散步。河边,冬阳下,提笼架鸟的老者,活泼可爱的孩子,相依相偎的情侣,各行其道。落叶,枯草,阳光,声音,清冷的河面,细小的忧伤,来自生活的活色生香。
被摇落的枝叶,反复经历着生死。阳光温和,我已人到中年。
(四)
我一直留意楼前那株法桐,岁末了,它身上的叶子还没落完,很多悬铃还在。
它至少十几岁了,我搬到这个小区居住时,它就在楼前。当年,它只有铁掀把那般粗细。那是2008年春天,似乎很近,却又遥不可及。
显然,它早已适应了这里。十几年了,它还在。万物生而平等,只是命运不同。也许,不等它的叶子落完,春天就来了。到时,它会发出新的枝叶。新鲜的,陈旧的,地下的,地上的,消失的,存在的,并肩走在季节边缘。
一棵树的悲欢,谁会讲给你听?风从枝叶间拂过,多么好。
寒尽又一春。我想,假如来生我是一株植物,我一定要在荒草丛生中找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