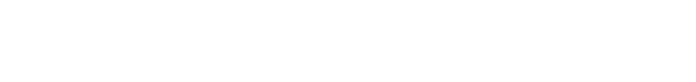□ 周德富
狮城环城路边半山腰上一幢歪斜废弃的小板壁屋里。
“哎,芳芳……”她从脏腑中迸出一缕微弱而颤抖的声音。十几年来,这个矮小、消瘦、干巴的老妪一直无偿使用着这幢年久失修的小板壁屋。
“芳芳……芳……芳……”她竭尽全力,却有气无力。
“吱嘎——”门推开了,夕阳的余晖照射进屋里。一个身材矮小、容颜憔悴的姑娘手提一根扒拉垃圾的铁棍,背着一篓垃圾堆里捡来的矿泉水瓶、易拉罐走了进来,立即奔到老妪床前,单腿跪下,叫一声“娘”,眼泪刷刷滚了下来。
“芳芳……你,你总算……总算回来了!”
“娘!”芳芳泪如雨下。
一条枯槁松弛的胳膊无力地从脏兮兮的棉被里伸出来,死死拽住盖在胸前的被角。
“撕!撕!”老妪像是恳求,又像是命令。
芳芳战战兢兢去撕那被角,但太结实了撕不动。老妪喉咙里梦魇般地嘟囔着:“23年前……我向郑奇……借过7万块钱……至今没……”油尽灯灭,老妪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可一双翻着白眼仁的眼睛仍大大地睁着,青筋暴露的双手依然死死抠住被角。
芳芳“哇”地号啕大哭起“干娘”来。十几年前,老妪把她捡了回来,二人相依为命。清冷煞白的月光从破窗户照射进来,屋外的风也跟着呜咽……
“也许只有找郑奇爷爷能帮忙料理一下。”芳芳擦干眼泪,喉咙“咕噜”了一声,点燃半截蜡烛开始在身后的板壁上搜寻着。肮脏的板壁上用粉笔头写着一串串密密麻麻、东倒西歪的数字,她像大海捞针一样从中找到了一个手机号码。
芳芳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干娘的丧事有着落了!芳芳跑去电话亭打完电话,悻悻地回到死去的干娘身旁,心里七上八下地翻滚着一个又一个疑惑:郑奇真的能来吗?安葬干娘要用多少钱?殡仪馆愿意火化一个身无分文的拾荒者吗……夜渐深、渐静了,芳芳在干娘脚边点燃一对白蜡烛,几张纸钱在干娘遗体旁燃烧着。
芳芳一只手吃力地扳干娘的手指,一只手使劲扯揉皱的被角:干娘那铁耙似的10根指头,纹丝不动。芳芳扯断了被角上的棉线,扯开一道半尺长的裂缝。
芳芳目光落在裂缝上,黯然的眼睛顿时射出惊喜的亮光。缝隙处露出一叠用塑料薄膜包裹的钞票:尽是些5元一叠、10元一叠的“散碎银子”。
晨曦从小窗口透了进来,照在死者脸上。那张苍白枯槁的面孔,似乎把芳芳从梦幻中唤醒过来,又仿佛回到一个梦幻中去。“吱嘎——”门推开了,郑奇带着一高一矮两个手拎着香蜡纸烛的小伙子走进来。郑奇面对芳芳干娘的遗体,不断摇头、叹息。一番唏嘘之后,他拿出一些钱,吩咐高个子立即去联系椅子山殡仪馆处理火化事宜;又叫矮个子去向当地办事处报告及购买丧事用品。
郑奇跪下叩3个响头,上3炷香,烧几张纸钱,哆哆嗦嗦从怀里掏出一张借据,泪眼婆娑地念叨:“你男人临走时托付我好生照顾你,我没做到。也怨你脾气太倔强,不愿受人恩惠,非得独自跑城里受苦受难,还说非得要还我那7万块钱。你一个妇道人家,能不受冻挨饿就算万事大吉了,哪还有钱来还我?现在你走了,人死账清,你应该安安心心、无牵无挂才是。这是你执意要打给我的那张7万块钱的借据,今天当着你的面烧了,我们谁也不欠谁的。不!我欠你男人的债,永远也还不清!你轻轻松松上路去极乐世界安享太平吧!”
郑奇一面说一面点燃那张借据,饱经风霜的老脸热泪纵横……
干娘的丧事办完,郑奇带着两个小伙儿走了,只字不提丧葬费用之事,只是木讷地不断重复念叨这句话:“是他男人把我从塌方煤窑里推出来的!是他男人把我从塌方煤窑里推出来的……”
头七刚过,芳芳又给郑奇打电话。她把干娘藏在被子里的钞票全部取出,一叠一叠整整齐齐地码好,总共六万六千五百元,还差三千五百元才够七万元。芳芳把钱堆放在床上,用自己的小被子盖着。这回,她拿定主意,不管郑奇爷爷怎么谦让,也一定要他把钱带走……所欠三千五百元打欠条给他,保证到年关帮干娘一个子儿不差地把债还上……